在堆满书籍的东京寓所里,墙上钉着约翰·福特与让-吕克·戈达尔的照片,88岁高龄的影评人、作家、学者莲实重彦带着狡黠的微笑坦言:此刻其实不太想谈论小津安二郎。我们本是为其著作《导演小津安二郎》英文版问世而来,但这位老者的思绪却萦绕在古典好莱坞。他交替使用日语与略带法国腔的英语说道:“这本书写于四十年前。我最后的专著是关于约翰·福特。而这才是我最新著作。”他指向《何为镜头?》(ショットとは何か)说道:“所以,我已离小津太远。”
诚然,本月即将迎来米寿的莲实依然笔耕不辍。茶几上散落着他近年以多国语言出版的电影论著——这不过是莲实庞大创作版图的冰山一角,除电影批评外,更涵盖法国文学哲学研究(他获索邦大学博士学位)乃至三岛由纪夫奖获奖小说。尽管著作等身且在日本备受推崇,英语世界却仅能零散读到其文章。幸得瑞安·库克翻译、加州大学出版社今岁推出的《导演小津安二郎》,终使这一缺憾得以弥补。当莲实的思绪已远游至其他导演,我们这些初窥其英文世界的读者,自有充足理由珍视这部里程碑著作的面世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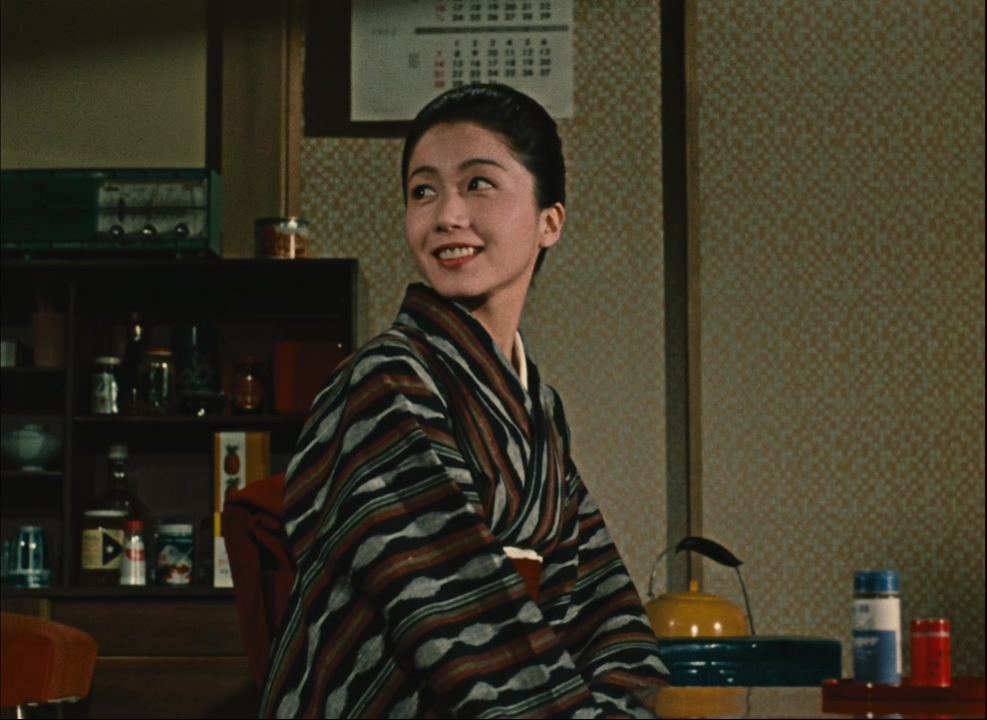
1983年首版的《导演小津安二郎》已成为日本影史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。书中莲实提炼出小津电影中反复出现的“主题系统”——如“进食”或“发笑”等行为姿态——揭示其直面电影本质的创作方式。莲实着重分析“银幕所见之物”,拒斥以先入之见(对小津的、对日本性的、对其他非电影语境的)干扰观影体验。借此,莲实直指唐纳德·里奇、保罗·施拉德等西方学者对小津的误读:小津绝非极简主义者;其电影无关“物哀”;所谓“枕镜头”亦非游离叙事之外。以自信笔触与惊人洞见写就的独特文本,令《导演小津安二郎》影响数代日本及海外影迷影人变得顺理成章。正如学者亚伦·格罗在序言所言,此书不仅是小津创作论的解谜,更是对“电影之所以为电影”的本体论探索。
访谈内容
NOTEBOOK:著作初版已逾四十年,如今得见英译本问世感受如何?
莲实重彦(以下简称莲实):(英语)非常高兴。衷心感谢译者瑞安·库克。(日语)虽未通读英译,但确信其远胜法文版。
NOTEBOOK:对多数英语读者而言,此书将是认识思想家莲实重彦的初体验。您期待海外读者如何进入您的世界?
莲实:(日语)首先请忘却小津是日本导演。诚然他生于斯长于斯,但毕生挚爱实为好莱坞电影。真正的作者超越性别与国界。我试图仅通过银幕分析,理解这个无国籍的作者。因此书中或有令美国读者不适之处——我冒犯了不少德高望重的学者影人。结果小津虽获广泛认可,但我眼中的他绝非国际化的日本导演。当下我认为真正代表日本国际形象的唯有黑泽明。而这般评价暗含对黑泽的不屑。《七武士》(1954)对好莱坞实有不良影响。

NOTEBOOK:您曾详论黑泽明吗?
莲实:没有。他固然优秀,却非小津般的异数。另一异数当属沟口健二。沟口与小津皆超越国族与时代,直面电影本质。另一位我极欣赏的是黑泽清。毕竟他师承我钟爱的理查德·弗莱彻。这是个怪才导演,却系出名门。
NOTEBOOK:您在序言提及,本书缘起1981年为国立电影中心(现日本国立电影资料馆)小津回顾展撰写解说,时距小津逝世近二十年。这段经历如何催生此书?
莲实:最初动笔是为疏解少年郁结。我初高中时,小津没有获得如今日般的尊崇,反被视为保守、男权、不合时宜。若其电影真以男性为中心,何以让女性持枪示人者竟有两部?这些都来自好莱坞的影响。当时的人并没有这样一些理解,所以将视其为很纯粹的日式导演。
NOTEBOOK:您认为《导演小津安二郎》出版后,日本对其评价发生何种转变?在美国,唐纳德·里奇将小津视为“最日本”导演的观点仍影响深远。
莲实:通过此书,人们得以认知作为作者而非日本代表艺术家的小津。其电影表达的只是肉眼可见之物。
NOTEBOOK:您对小津作品的分析聚焦于“主题系统”的提炼。此方法论如何形成?
莲实:极其简单——源于所见。初观小津便注意:啊,这些人都在齐笑;他们列队而行;女性突然解下围巾。此类细节扑面而来。虽有人指其电影男性贬抑女性,但片中妻子收拾丈夫衣物时,有人会刻意将衣物摔落地面。[此为莲实书中指认的“显著例外”,却仍“构成系统的连贯性”。——编者注] 这般处理前所未见。

NOTEBOOK:故小津电影特具启发性?
莲实:(英语)没错。
NOTEBOOK:这一方法也用在约翰·福特等导演研究上吗?
莲实:主题分析法相通。如约翰·福特电影中,人人都在投掷物品。
NOTEBOOK:故章节标题或为“投掷之物”。
莲实:正是。(笑)
NOTEBOOK:您视此书为电影理论著作吗?电影本体论贯穿论述——理解小津即理解电影本质及其边界。
莲实:(日语)我不认为电影存在理论。自诩电影理论家者,不过将观点包装成理论。其思维与电影本体相去甚远,却自诩正确。例如我极敬爱爱森斯坦导演,却对其理论嗤之以鼻。
NOTEBOOK:您提及福楼拜“固有观念”(idées reçues)概念,用以讨论“观看”电影本貌之难,此于小津论尤为重要。
莲实:这样一种表述略带戏谑。但众人对小津的趋同认知,确实类似于福楼拜十九世纪提出的《固有观念辞典》。
NOTEBOOK:福楼拜研究与法国文学修养如何影响您的电影认知?
莲实:(英语)毫无影响。因我接触电影早于福楼拜。十二岁便痴迷西部片导演。初识异国风物始于电影,而非法国文学。
NOTEBOOK:请谈您的文风。滨口龙介称此书“宛如小津电影”,是“小津体验的有机组成”——仿佛此书亦由小津执导。
莲实:(英语)他极聪慧。(笑)
NOTEBOOK:写作时有意营造“小津执导”的风格吗?
莲实:并非是刻意为之,纯属自然。

NOTEBOOK:您从事影评数十载,更通过写作与教学影响数代日本影人。小津电影对当代导演有何启示?自称受其影响者甚众。
莲实:(日语)这难下定论,因为当下已不是自然接触小津的语境。“观看小津”已成刻意之举,最好状态应是偶然步入影院得见其作。(英语)如我初识威廉·韦尔曼。这位杰出导演并不张扬,场面调度却臻完美。第一次看其作品时并不知其名,仅是觉得佳片难得。(笑)
NOTEBOOK:您曾阅读戈达尔、特吕弗等《电影手册》派作者论吗?
莲实:(日语)是的。与1960年代法国新锐影人的相遇实属不幸——我厌恶他们奉若神明的安德烈·巴赞。他在文中比较约翰·福特与威廉·惠勒,竟称后者更优。虽然巴赞后来自承谬误,但这一错误已然荼毒甚广,这使我与《手册》派关系复杂。当然我深爱戈达尔,而他也钟情福特。但特吕弗等曾视福特为劣导。等到福特辞世,这些才意识到福特电影的奥妙,这些都是巴赞早年谬论种下的恶果。即便年少时,我亦自信比他们更懂好莱坞。

NOTEBOOK:好奇您如何炼就慧眼。您的影评极重银幕实相,而洞见实非易事。当然这些或是天赋使然,但可有诀窍?当年撰写如此精微的镜头分析时,并没有家庭录影带可供反复观看,如今想来简直不可思议。
莲实:(英语)年轻时每周观片二十部。力求阅尽天下电影。总念“此秒于我即是永恒”,所以我全盘接纳银幕的馈赠。
NOTEBOOK:您仍大量观影,包括新作。对当代日本电影评价如何?较之他国电影有何异同?
莲实:最新一期《电影手册》(取桌上杂志)竟在发掘小津未发行旧作。这是为什么呢?实难理解。想要观看小津,本可赴伦敦、阿姆斯特丹、布鲁塞尔——但这些地方无人问津。可知相米慎二?二十五年前我为《电影评论》撰文推介,然法国人迟至今日方“发现”相米。
NOTEBOOK:法国将上映哪部相米作品?
莲实:《搬家》(1993)。
NOTEBOOK:相米的《台风俱乐部》(1985)与《鱼影之群》(1983)去年刚登陆美国。
莲实:很好。相米之名能够传播开来对我来说是件快乐的事。
NOTEBOOK:如何看待当今日本导演?
莲实:滨口龙介自不待言。三宅唱亦佳。纪录片导演小森遥与小田香皆出色。
NOTEBOOK:再请教小津相关问题。《东京物语》(1953)似较其他作品更受推崇。《视与听》影史佳片评选中,该片自1992年起稳居导演/影评人票选前五。您对此作何想?
莲实:首先我厌恶“十大佳片”之流。虽曾多次回应此类评选,但确实难以苟同。《东京物语》近乎完美,却正因完美令我不喜。

NOTEBOOK:您个人最爱小津哪部作品?可有特别意义之作?
莲实:(日语)最爱《那夜的妻子》(1930)。
NOTEBOOK:缘由是?
莲实:(英语)因其极具好莱坞神韵。
NOTEBOOK:此为首部英译著作。您最希望哪部作品接续译介?我私心期待《约翰·福特论》。
莲实:没错。约翰·福特,约翰·福特,约翰·福特。
NOTEBOOK:最后关于小津的寄语?
莲实:(日语)我常常思考,假如与在世时的小津相遇能否聊到一起。但转头一想又觉得很可怕。因为银幕外的小津享受人生——与女优交游,与艺妓往还——但我心中的小津只是创作电影的小津。故我深爱其电影的程度,或许远超导演本人,恐怕他无法理解这些想法中的深情。
作者:K.F. Watanabe
来源:MUBI
来自豆瓣用户: 三仛

